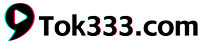责任编辑: deichai.com
劳拉•努南(Laura Noonan),纽约市
曼哈顿下城的9/11纪念馆水池四周如今冷冷清清。曾经从早到晚都在这里涌动的人群不见了。3月,这里竖起了一道围栏,把人们挡开;此外,自从曼哈顿成为新冠疫情的全球震中以来,大多数游客也不再敢来这里。
在安保人员的允许下,早上会有一小波游客来访,人人都要全程戴着口罩。参观完毕后,游客可能会信步前往附近的华尔街,那里的上班族正在慢慢回到曾经拥挤的写字楼,或者再往前走一点,到达曼哈顿最南端,那里的游船已复工,把游客带到靠近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的水域。
他们会发现,在著名的华尔街铜牛前拍照、或者在附近的餐馆和星巴克(Starbucks)找位子变得更容易了。他们不必再费力挤进拥挤的地铁,也不必排队等候红色双层观光巴士,载着他们游览曼哈顿的景点。

他们会发现新乐趣,比如肉库区(Meat Packing District)及其他地段冒出的漂亮的户外就餐露台,以及遍布市内公园和绿地的各类健身班。
他们还会发现本地人最近变得好客了。曾几何时,游客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猫途鹰(TripAdvisor)推荐的纽约热门观光地的人来说是一种麻烦,但如今,游客很受欢迎,他们是资金拮据的企业急需的收入来源,也是纽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创伤期之一后,生活开始恢复正常的一个迹象。
如今的游客们或许会觉得纽约安静得令人不安;摇滚明星乔恩•邦•乔维(Jon Bon Jovi)最近谈到了在那里拍摄音乐录影时“超现实”和“吊诡的”体验。但我们这些在疫情高峰期留在这里的人,记得这座城市更加吊诡的样子。
3月16日晚,我从都柏林返回纽约,几小时后,美国实施了一项旅行禁令,将英国和爱尔兰加入那些旅行者(基本上)被禁止入境美国的欧盟(EU)国家的行列。
当时,欧洲被视为新冠疫情热点地区。新冠病例已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激增,其他国家也开始战战兢兢。在我的祖国爱尔兰,学校在前一个周五停课了,我们在几天前刚进入保持社交距离的时期,大家把抗菌凝胶抹在所有东西上。
我回来的头几天,纽约基本上表现得像不会受到疫情影响似的。由于刚从欧洲返回,我不得不在家工作,公立学校也被勒令停课,不过大多数上班族仍在办公室上班。餐馆和酒吧人头济济;问候时,人们互相亲吻和拥抱。
接着,一切都变了。

到了那个周末,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病例数急剧攀升,随着有些人不仅得病了,而且病情恶化,甚至死了,纽约实施了封城。该市关闭了酒吧、咖啡馆、健身房和几乎所有的商店。
百老汇(Broadway)的灯熄灭了。时代广场(Times Square)的灯还亮着,但几乎没人在那里欣赏。地铁仍在运行,但除非别无选择,大多数人都不敢靠近。
我住在曼哈顿最繁忙的主干路之一——西街(West Street)。之前一年半,我的公寓永恒(而且时常令人恼火)的背景音是汽车喇叭声和引擎轰鸣声,还有楼下9/11纪念馆传来的舒缓流水声。
到了3月下旬,水池关闭了,警笛开始不断鸣响,救护车在曼哈顿岛上穿梭,忙着抢救病人,当时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于新冠病毒。
过去,这座城市似乎无边无际,而现在纽约变成了我只能步行或跑步前往的一个个地方,因为当时即使是该市的共享单车计划似乎也风险太高。我一大早沿着黑暗、空寂无人的哈德逊河跑步。
到了晚上和周末,我就散步——因为这是唯一能做的事。疫情爆发前,我总会在河边散步,吸引我的是河水和自由女神像动人心魄的美景,以及壮观的布鲁克林大桥和曼哈顿大桥。
疫情期间,不少人在河边活动,而人是需要避开的。我发现了曼哈顿下城区腹地迷宫般的街道、美丽的庭院、精致的建筑,全然是一个我以前不知道存在的世界。周末时,我会走得更远,要么沿着哈德逊河走到曼哈顿上城,要么穿过布鲁克林区。
其中一些探索游的所见所闻提醒我纽约变成了什么样子,另一些则鼓舞我对这座城市永恒的精神保持信心。

复活节的周末(4月11-12日),我沿着西区(West Side)往北跑步,然后转向中央公园(Central Park)。这条路线经过纽约最繁忙的医院之一。医院外搭着白色帐篷,还停着冷藏车,它们被用作临时停尸房,那种帐篷让你想尽快跑回家,不再出门。
有一个周六,我走到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那儿离我的公寓足有六英里。我穿过附近的居民区,孩子们在那里画画,然后把画贴在褐沙石房屋的玻璃窗上,许诺:“日子会好起来的”。
我的家人,我见到的唯一知道我名字的人,是公寓楼的几个门卫,尤其是路易斯。在那些最糟糕的早晨,他们都会对我说声:“早上好”。
我还记得附近星巴克重新开业的那天。4月中旬的那天,我几乎是偷偷摸摸地排队,等着拿到以前每天都喝、而那时已有五周没喝上的咖啡。我记得我和那些同命相连的人聊着天,他们也在等自己在网上下的单。
我记得当时想到,他们跟我一样,在其他人成群结队逃往父母家、度假屋、在爱彼迎(Airbnb)租的房子时呆在纽约。
我记得之后几周,星巴克的员工们在我们的咖啡杯上写下的祝福。在星巴克及其他许多重新开张的商店的橱窗上,贴着员工们写给顾客的便条,上面写着他们看到我们回来是多么高兴,以及这一切将会过去。
到了初夏,餐馆和酒吧针对延长禁止室内就餐的指令,将街道变成了欧式广场。这一幕当时是——如今仍是——美丽的,这座城市让人觉得在恢复元气,将疫情初期的恐怖抛诸脑后。
这种“即使拿到一手烂牌也要尽量打好”的决心,以及纽约人的精神和团结,支撑这座城市度过了这场大流行,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后的抢劫与破坏行为。
话虽如此,伤痕还在,而且很多人担心这些伤痕将持续存在。
纽约实施封城6个月后,许多酒吧、餐馆和酒店仍然停业。其中一些店永远不会再开门。人们正在离开这座城市,不仅是为了避开这场大流行,而是一去不复返。公寓空置率创下历史新高,8月曼哈顿有1.5万套空房。游客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
达维德•吉廖内(Davide Ghiglione),罗马
5月初解除封锁后,我第一次冒险进入罗马市中心,感觉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我前往的第一个地方——也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广场之一——近乎空无一人。

这个通常繁忙的景点不见了在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7世纪意大利雕刻家——译者注 )雕刻的四河喷泉(Fountain of the Four Rivers)前自拍的游客、卖肖像画的艺术家、以及躲不开的街头小贩。少了游客们的踩踏,鹅卵石间长出了青草,为广场平添了意想不到的色彩。
我第一次能听见水从石灰华海神们的口中和广场中心方尖碑下的岩石中涌出的哗哗声。
和许多住在罗马的人一样,我自私地为能够独享这个美丽的地方感到快乐。突然间很难相信,纳沃纳广场之前一直是当地人避开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游客汇聚的景点,就像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或纽约的时代广场,有着定价过高的餐馆和混乱的人群。
谁也想不到有一天游客竟然会不来了——尤其是广场周边餐馆、酒吧和咖啡馆的老板们。

但其中一家餐厅Camillo,抓住封锁带来的得天独厚的时机,迅速转向一个新的客户群体:回归空荡荡的市中心的罗马人。在5月底重新开业时,原来的游客菜单已被一份全新的菜单取代,菜品经济实惠、时尚新潮、优质食材。
主菜7欧元起,还可提供较小的盘子供顾客们分享。此外,老板们还推出“Drinketto”,一种售价3.5欧元的外卖开胃酒(相比之下,封城前饮品的售价为9欧元)——如今这种小甜酒很受来市中心逛的当地人欢迎。
目前的菜品仍包括芝士胡椒意面(cacio e pepe)等经典罗马菜,但在培根蛋酱意面(carbonara)等最受青睐的传统菜品中加了点新创意,把面身炸成松脆的立方体——引爆了口感,还有“Lasagnetta Funk”,这是一种加了埃塞俄比亚香辣牛肉碎的小份千层面。
30多岁的罗马市民保罗•瓦亚诺(Paolo Vaiano)与朋友们坐在一起小酌一杯巴贝拉(Barbera),这是一种产自皮埃蒙特大区(Piedmont)的醇厚红酒,他说,很高兴终于能够享受到本地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就在两个月前,还无法想象能在这里度过一点休闲时光,或在某家餐馆吃点像样的东西,这些餐馆似乎只迎合不懂意大利菜的游客。”他补充道。“但现在我们在这里——谁能想得到呢?”
内森•布鲁克(Nathan Brooker),伦敦
最初,伦敦市中心的街道安静了。接着那些玩滑板的人出现了。这些人顽强得就像核灾难后出现的蟑螂。他们来到街道上,在朋友们的注视下,沿着扶手滑来滑去并做出跳跃动作。没了游客,也很少看到上班族,街道成了他们的舞台。

夏末,随着酒吧和餐馆老板们将桌椅搬到户外,苏豪区(Soho)的街道又有了饮酒者和食客。捱过死气沉沉的封城期,看到伦敦人又出门寻找乐趣,那一幕让人宽慰。
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在9月参观英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的经历。参观者必须预订一个参观时段,佩戴口罩,而且美术馆设计了三条单向的参观路线,以帮助参观者保持社交距离。但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信步走了大约10分钟后——自11岁时首次随学校参观国家美术馆以来,我会不时回来看看——感觉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或者说近乎恢复正常。“是不是很棒?”我听到一位参观者在特纳(J. M. W. Turner,英国浪漫主义画家——译者注)的《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The Fighting Temeraire)对她的朋友说。“没有游客!”
她说的有道理。一年前,展厅里会挤满紧握手机的度假客,他们忙着“收集”馆里最著名的画作,仿佛在玩《口袋妖怪GO》(Pokémon GO)。没了他们,美术馆显得很宁静。氛围好极了。
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当我走到《梵高的椅子》(Van Gogh’s Chair)时,我隐隐开始想念那些游客了。毕竟,一座美术馆有人参观才是最好的。我记得有次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看到一对少男少女情侣从进门就开始吵架,一直吵到出门;我的印象是他们都没抬头观赏任何艺术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Air and Space Museum)的餐饮区,我曾目睹史上最逗趣的事儿之一:一位穿着纱丽的老妇人试图——违规地——在自助饮料站加满她的水壶,但不知道怎么推动释放饮料的机械臂。
她认为设备坏掉了或者是空的,就一个一个尝试,雪碧、可乐、健怡可乐,她试遍了所有的龙头,直到终于找到个能用的——然后往自己的水壶里接了一坨热的黄芥末酱。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没了游客,国家美术馆尽管更宁静了,但却略显寂寥。
译者/偲言
文章编辑: deichai.com